close
西北科學考察團90周年:萬裡向西行
時事艱難,國傢不靖。中國學人在如此環境中,仍義無反顧地獻身科學事業,不能不令今人感佩。
西北科學考察團營地及駝隊。
考察途中,地質學傢袁復禮(左)、外方團長斯文·赫定(中)和中方團長徐炳昶(右)在談工作。
考察團招收的四名學員,左起依次為崔鶴峰、劉衍淮、馬葉謙、李憲之。其中,劉衍淮、李憲之後來經氣象專傢郝德推薦留學德國,成長為著名氣象專傢。令人惋惜的是馬葉謙在考察途中不堪忍受孤獨自殺身亡。
1927年5月9日,一支由中外科學傢共同組成的考察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登上前往包頭的列車。他們此行的路線是經包頭、百靈廟至額爾濟納河流域,最終到達新疆腹地。與以往由外國人主導的考察團不同,這次的考察團是中國和瑞典科學傢聯合組成的。近代以來,中國人第一次以平等的姿態與外國科學傢一起進行科學考察活動。
出發前,主辦方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理事長周肇祥給每個團員手裡塞瞭一張紙,上面是他專門為團員們寫的送別詩。瑞典大探險傢斯文·赫定說:“他的‘不朽之歌’就仿佛是此後我們合作征途裡所充溢著的那種親情與和諧之音的一個序曲。”
在此後的8年時間,考察團的中外團員精誠合作,互相扶持,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取得瞭令世人炫目的成就。
“大百科全書”上寫錯瞭
2017年12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學與絲綢之路——西北科學考察團九十周年紀念展”在北京大學開幕。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徐炳昶先生之女王忱,作為嘉賓出席瞭開幕式。
開幕式現場,88歲高齡的王忱顯得非常高興。這已經是她今年參加的第二個紀念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展覽瞭。10月中旬,“萬裡向西行——西北科學考察團90周年紀念展”剛剛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落下帷幕。學術界和公眾對於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認知度,與上世紀80年代她剛開始研究這段歷史時,不可同日而語。
1985年,王忱剛剛離休。有一天,她的弟弟徐桂倫在《人民畫報》上看到一則圖片說明寫道:白雲鄂博鐵礦是我國年輕的地質學傢丁道衡1927年隨外國考察團西行時發現的。
王忱和徐桂倫感到十分詫異。他們從小就聽母親講父親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深入西北腹地科考的故事。王忱記得,那時傢裡有一本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大相冊。相冊裡,黃沙、駝隊,還有父親騎在駱駝上的身影,像童話故事一樣,引發瞭她無限的遐想。他們從小就知道,西北科學考察團是一支中國考察團。半個多世紀後,人們怎麼會把它當成外國考察團瞭呢?
經過調查,王忱發現這條錯誤信息來源於中譯本《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連“大百科全書”都寫錯瞭,王忱感到,自己有責任將這段史實搞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於是,從那時起,她便投入到搜集和整理西北科學考察團資料的工作中。
王忱告訴記者,“大百科全書”中出現這樣的錯誤,也不能怪編輯馬虎。1935年科考活動結束不久,中國就陷入瞭抗日戰爭。國傢危亡,人民流離失所,科學研究成為不可企及的奢望。
而瑞典則是少數幾個沒有卷入二戰的國傢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瑞典科學傢對這次科學考察的研究工作,從未中斷。他們陸續發表瞭50多卷與這次科考活動有關的專著。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有一本著作問世。
1949年後,西北科考團的中國隊員們曾計劃聚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考察成果。可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有人認為這次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是配合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行為。科學傢們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再提這事兒瞭。幾十年來,他們雖然在各自的科研崗位上做出瞭很多貢獻,但是始終沒有對這次科學考察進行系統的研究總結。正因如此,很長時期以來,人們對這次科考活動的瞭解都來源於瑞典科學傢的著作,中外學術界都以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是一個外國考察團。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撥亂反正,人們才有可能客觀地研究這次偉大的科考活動。
被抵制的“翁-斯協定”
最早提出深入中國西北腹地進行大型科學考察的,是瑞典地理探險傢斯文·赫定。
在瑞典,斯文·赫定的名字,婦孺皆知。他與諾貝爾一樣,是瑞典國寶級的科學傢。1865年,斯文·赫定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個中產階級傢庭。不過,赫定並沒有像父輩那樣,過循規蹈矩的安穩日子。15歲那年,他見証瞭瑞典極地探險傢諾登斯科德從北冰洋凱旋的盛況。從此,去地球上那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探險,成為他的人生目標。
1888年,斯文·赫定師從德國地理學傢李希霍芬。對於“李希霍芬”這個名字,大部分讀者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是他提出的一個概念,卻被人們廣為熟知,那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1868年至1872年,李希霍芬遊歷瞭大半個中國。他一路走一路寫,將沿途的風土人情、地理地質都記錄下來。考察結束後,他花費瞭大半生的精力,撰寫瞭5卷本的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這本書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征的著作。在該書第一卷中,李希霍芬提出瞭“絲綢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的研究方向,對斯文·赫定產生瞭極大影響。1890年,博士畢業不久的斯文·赫定,便以翻譯的身份開始瞭第一次深入亞洲腹地的考察。
到20世紀20年代,斯文·赫定已經先後四次到中國西北考察。在歷次考察中,他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00年他發現瞭早已消失的樓蘭古城。
憑著豐碩的考察成果,斯文·赫定贏得瞭巨大的國際聲譽,但是他並不打算就此停下腳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率領一支龐大的綜合考察隊,重新踏上中國西北部那塊神秘而荒涼的土地,發現更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1926年汽車監控系統,機會來瞭。
這一年,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計劃開辟從柏林到北京、上海的航線。開辟一條跨越歐亞的遠距離航線,需要預先考察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氣象情況。曾經四進四出中國西北腹地,有著極高聲譽的大探險傢——赫定無疑成為率領這支考察隊的最佳人選。盡管赫定當時已經年過花甲,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接受瞭漢莎公司的邀請。
經過商定,漢莎公司為赫定的探險隊安排瞭幾名航空技術專傢、一名氣象專傢、一名攝影師和一名會計﹔赫定則召集瞭幾名地質學、考古學者。他們計劃先騎駱駝,在航線沿途實地走一遍,再派飛機進行飛行考察,最後實現從柏林到北京的首飛。考察期間的一切費用都由漢莎公司提供。
對於這次考察,赫定非常興奮。他終於有機會將前幾次考察中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搞清楚瞭。
1926年11月,他帶著德國航空專傢錢默滿來到北京。
當時,奉系軍閥張作霖把持北洋政府,其統治正在風雨飄搖之中。南方的北伐軍節節勝利,不少文化名人選擇南下。在這種局勢下,北洋政府根本無心考慮什麼科學考察活動。
斯文·赫定找到瞭自己的瑞典老鄉、時任中國農商部礦政顧問的安特生。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質學和考古學傢。1914年,他應邀來華,幫助中國尋找礦產。十幾年間,他不但發現瞭仰韶文化遺址和周口店遺址,而且與中國官方和學術界建立瞭良好的關系。
11月底,在安特生的帶領下,赫定見到瞭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希望翁文灝能夠幫助考察團拿到中國政府的批準。
翁文灝不僅是我國地質學界的先驅,而且是一位很有眼光的科研組織者。在此之前,他組織地質調查所對陝西、甘肅等地做過不少地質調查工作,但還從未進入新疆做過考察。如果中國科學傢加入赫定的考察團,將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一書中記錄,翁文灝提出要派兩名中國地質學傢和一名考古學傢參加考察團,並且要求所有古生物學的考察結果,必須發表在北京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月刊上。
對此,斯文·赫定欣然接受。於是,在翁的引薦下,赫定很快與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長王蔭泰聯系上。
外交部擔心軍方反對,沒有同意赫定做飛行考察的要求,但是對他率領駝隊考察的要求,很快便批準瞭。赫定甚至還見到瞭張作霖。張作霖雖然嘴上說“我不懂這些讀書人的事”,但還是答應寫信給新疆督軍楊增新,幫考察隊掃清新疆方面的障礙。
1927年2月,赫定考察隊的領隊拉爾生開始在包頭招兵買馬。考察所需的兩百頭駱駝、帳篷、糧食、奶酪、糖、鹽、茶等,一一採買備齊﹔隨隊的廚師、馬夫、隨從等工作人員也雇好瞭﹔幾名德國和瑞典的科學傢先後來到北京。萬事俱備隻欠東風,考察隊眼看就要出發瞭,可社會上的反對聲浪卻日益高漲起來。
3月5日,北京大學國學門召集清華學校研究院、歷史博物館、京師圖書館等11傢學術機構的20名代表,在北大三院召開會議,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反對翁文灝領導的地質調查所與斯文·赫定簽署的協定(簡稱“翁-斯協定”)。
為首的沈兼士、劉半農、徐炳昶等學者,對其中兩條尤為不滿。一是隻允許兩名中國學者參加,限期一年返回﹔二是將來採集的歷史文物,要先送瑞典研究,等中國有條件以後再送還。他們認為這種協議“有礙國權,損失甚大”。
赫定感到,反對派的出現猶如晴天霹靂,完全擾亂瞭他們的計劃。他在3月13日的《益世報》上宣稱:“(中國學人)在疑敝人欲將中國歷史資料與藝術遺物盡量攜取。茲特奉告,敝人匪惟絕無攜取此等器物之意,且對開會諸君所宣示者,極表贊同。蓋敝人曾向中國政府自動提出,以此行所獲歷史遺物,全數留存中國,足以証明之也。”
不難看出,中國學者中流傳的“翁-斯協定”與斯文·赫定口中的“翁-斯協定”,存在很大出入。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呢?
西北科學考察團研究會副會長徐十周告訴記者,時至今日也沒有人見過“翁-斯協定”的正式文本。也許“翁-斯協定”尚在擬定中,部分內容流傳出去,引起瞭中國學人的抵制,這份協定便胎死腹中瞭。
那麼,“翁-斯協定”到底是怎麼規定的呢?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王新春通過比對史料認為,“翁-斯協定”大致有以下內容:考察團為瑞典的探險隊,由斯文·赫定擔任隊長,全權負責﹔中方派出兩名地質學傢和一名考古學傢參加,由斯文·赫定領導和安排工作,並接受其評判﹔中方學者負責與地方政府交涉﹔考察期限為一年﹔古生物方面的研究成果發表於《中國古生物志》……搜集品方面,無脊椎動物化石全部留在中國﹔植物化石和脊椎動物化石中瑞兩國平分,但以瑞典為優先﹔歷史考古遺物先交中國保存,然後將副本送給瑞典﹔所有史前考古遺物中瑞兩國平分。
顯然,“翁-斯協定”並不像斯文·赫定辯白的那樣,要將“所獲歷史遺物,全數留存中國”。另一方面,“翁-斯協定”明確表示,西北科學考察團是一個瑞典考察團,中國學者隻是參與其中罷瞭。
徐十周認為,對中國學術主權的捍衛,才是中國學人群起抵制的關鍵。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西北的科學考察史是一部讓國人傷心的歷史。清末,歐美形形色色的探險傢,隨意深入我國西北腹地,考察我們的大漠綠洲、湖泊盆地。他們不但考察地質礦產、挖掘古生物化石,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盜取瞭許多文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對敦煌的洗劫。著名歷史學傢陳寅恪曾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不過,在徐十周看來,斯文·赫定與斯坦因、伯希和等文物大盜有本質區別,他更多的還是一位科學傢。正因如此,在後面的考察中,赫定才能與中國隊員結下深厚的友誼。不過,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向他發難時,他感到極為惱火。
“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3月10日,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12名代表第一次坐到談判桌前。赫定回憶,這次會面氣氛相當融洽。出席會議的劉半農和徐炳昶兩位教授,說一口流利的法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他絕不會想到,徐炳昶後來會成為中方團長,與他一同踏上西行之路。
中國學者們雖然彬彬有禮,但對於原則問題毫不相讓。直到這次會面時,赫定才搞清楚,原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考察團的主權。
赫定也算情商超高,立即提出將考察團改名為“北京學術團體聯合組織之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並建議考察團設立兩個團長,一個是赫定,另一個由中國學者擔任。
赫定對考察團叫什麼名字,歸屬權是誰,並不太在意。按他自己的話說:“野外艱苦嚴酷的生活將自動証實誰是真正的領導。”自負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對於搜集品如何分配的問題,他就沒那麼灑脫瞭。雙方對把古生物、地理、地質等方面的搜集品副本贈與赫定方面,沒有什麼異議,可在考古搜集品如何分配的問題上,陷入瞭僵局。
赫定認為,考古搜集品也應該像其他搜集品一樣,將副本贈與瑞典,可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認為,一切古物都必須歸中國所有,不得運出國境。
與學者們對主權問題分毫不讓相比,北洋政府卻沒有給中國學人任何支持。當外交部次長王蔭泰收到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書面抗議書後,反而讓手下給赫定帶話說:“不要理會除政府以外的任何人,政府已經答應給你們辦護照,而且完全站在你們一邊。”
有北洋政府撐腰,赫定絲毫沒有讓考察團延期的意思。3月22日,考察團成員帶著兩節載有40噸給養和設備的行李車,從豐臺火車站出發,向包頭進發。憤怒的學生揚言要將行李車掀出鐵軌,甚至要燒瞭他們的行李。為避免夜長夢多,考察團成員連夜乘坐列車離開瞭北京。
中國學者們得知赫定不顧談判還沒有結束就私自讓考察團出發,非常憤慨。第二天,赫定便收到瞭劉半農措辭嚴厲的來信。劉半農指責他背信棄義,根本沒有讓中國科學傢參與考察的意思,並警告,如果赫定敢擅自離京,就讓中國新聞界群起而攻之。
這時候,一直給赫定打氣的北洋政府也軟瞭。外交部對赫定說,鑒於事態激化,他們考慮要撤回考察團的旅行許可証。
3月23日這天,赫定住所的電話鈴響個不停,似乎所有人都想証實他是否還在北京,就連張作霖元帥府的人,也打電話告誡他,不要輕易離開北京。
事態的發展,令赫定措手不及。直到這時,他才不得不“放下身段”,認真與中國學術界進行協商。
3月25日,劉半農向赫定宣讀瞭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決議。內容包括:考察團被命名為“中國科學團體聯合會下屬赴新疆科學代表團”,不能再用“探險隊”的稱呼﹔中方將派出5名地質、考古、生物等方面的專傢和10名學生參加﹔代表團將有一個中方團長、一個外方團長(即赫定)﹔所有發掘物、科學觀察資料、筆記、照片等都要接受檢查才能發表﹔考古發掘物統一管理﹔團員不得私自購買文物,等等。同時,考察團一切費用仍由外方承擔。
這些決議,基本上都被赫定接受瞭,並成為他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簽署的19條合作辦法的雛形。
不過,剛看到這些條款時,赫定非常不滿。他對劉半農說:“你們一文錢不出,卻想把我們這次活動的所有科學成果都歸於北京的研究機構名下。然而,我還是要仔細考慮一下你們的建議,假如我解散探險隊並就此回國,也希望你們不要吃驚。”
其實,赫定才不舍得解散探險隊。漢莎公司出錢讓他重返新疆大戈壁完成未竟的事業,對他而言是求之不得的機遇。況且,當時考察團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給養、駱駝、工人都已經到位,可以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4月26日,赫定終於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在北大三院簽署瞭協議。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中寫道:
一切都定下來瞭,周(即會議主席周肇祥)和我與其他人一起在長桌旁坐瞭下來,我和周在兩份中文文本和兩份相應的英文文本上簽瞭字。周端坐在桌旁,用飽蘸墨汁的毛筆剛剛寫下一筆,一位攝影師按下瞭快門,閃光燈一亮。接著,我也用鋼筆簽瞭字。這一莊嚴的時刻將為後人所銘記。
雖然身為外國人,但赫定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刻對中國人而言意義非凡。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捍衛瞭自己的學術主權,結束瞭清末以來外國探險傢在中國任意掠奪文物,如入無人之境的現狀。劉半農甚至戲稱,這是一次“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某種程度上,西北科學考察團為此後中外合作樹立瞭典范。
萬裡向西行
協議達成,赫定恨不得立即出發。考察團的外國成員在包頭早已等得不耐煩,而且每停留一天就要多花費很多錢。但是中國考察隊員的名單還沒有確定,特別是誰來充當中方團長,一直懸而未決。
誰都知道,深入大漠進行科學考察,是一件前途未卜的苦差使。身為中方團長,不但要身體好,有膽有識,還必須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組織應變能力。而具備這些條件的中國學人,無不拖傢帶口,負擔沉重。
考察團即將出發的1927年5月,乃多事之秋。北伐軍節節勝利,北洋政府危如累卵,隨時都有崩潰的危險。張作霖不甘失敗,日益窮兇極惡。4月底,他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殺害瞭李大釗。一旦北伐軍攻入北京,北京城會不會遭戰火塗炭,誰也沒有把握。此時,拋開一傢老小,義無反顧地去參加科學考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討論中方團長人選時,大傢都沉默瞭。
好不容易跟赫定簽訂瞭協議,卻派不出中方團長,這無疑將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恥辱。就在此時,北京大學教務長、哲學教授徐炳昶站瞭出來。
徐炳昶(字旭生),1888年生於河南的一個書香之傢。1911年留學法國,1922年回國出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教務長。
他目睹國傢內憂外患,一直苦苦尋求救國之路。1925年,他與朋友一起創辦瞭《猛進》周刊,擔任主編,發表瞭很多針砭時弊的文章。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京報》曾披露過一份段祺瑞政府準備通緝的48人黑名單,徐炳昶與李大釗、魯迅等赫然在列。在與斯文·赫定進行談判的過程中,徐炳昶也一直是重要參與者。
徐炳昶自告奮勇出任中方團長後,在場的其他人都鬆瞭一口氣。劉半農立刻表示:“嫂夫人的工作我去做,生活問題我負責,你盡管放心走。”
要知道,當時北洋政府拖欠公務員和大學教授工資的問題非常嚴重。魯迅在《記發薪》中記載,1926年1月至7月,他隻領瞭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歷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達9240大洋。
人在北京都拿不到工資,人一走更不知道上哪兒去領錢瞭。當時,徐傢兩個孩子年幼,夫人是全職太太,尚有老母在堂。他這一走,不是一天兩天,傢中老小生活由誰來照料,的確是個問題。
徐炳昶之孫徐十物流車隊管理周說,為瞭幫徐炳昶解除後顧之憂,劉半農親自登門找到徐炳昶的夫人,保証按時發工資。後來,劉半農為這個承諾,著實費瞭不少的心力,但是徐傢還是沒有按時拿到工資,以至於徐炳昶在考察路上仍時刻惦記著一傢老小的生活。他在《徐旭生西遊日記》中寫道:“傢鄉離亂,北京薪水無著,恐怕皆在愁城中!”
時事艱難,國傢不靖。中國學人在如此環境中,仍義無反顧地獻身科學事業,不能不令今人感佩。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學考察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乘專車前往包頭,與等待在那裡的外國團員會合。這支由20多名科考隊員和20多名駝工組成的考察團,趕著200多匹駱駝,馱著400多箱行李,浩浩蕩蕩地踏上征程。
開始赫定對中方派一位哲學教授做團長,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徐炳昶不懂科學,還可能掣肘他的工作。可考察團出發後,赫定發現徐炳昶是一個正直坦率的人,他不但非常尊重赫定,而且坦率承認自己沒有科學考察的經驗。他對赫定表示,自己不會幹擾赫定的工作安排,隻要是為瞭科學,雙方的目標是一致的。
赫定在著作中表示,“徐炳昶是一位你所能遇到的最和善和最令人愉快的旅行伴侶。”“在我們全部合作期內,總有著一種最完美的和諧……他們(指中國人)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覺得,怎樣地不可少與珍貴。”
考察團到內蒙古大草原後,分成瞭3隊。北分隊是由瑞典、中國、德國、丹麥人組成的國際分隊﹔南分隊是由地質學傢袁復禮帶領、全部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分隊﹔大隊則由兩位團長親自帶領。
出發5個月後,科考隊領略到瞭大自然的威力,大隊一度幾乎陷入絕境。原計劃從額濟納到哈密月餘就可到達,他們事先帶瞭40天的糧食,可沒想到,在不見人煙的大荒漠中一走就是48天。
六十多歲的斯文·赫定在戈壁灘中膽結石復發,一病不起。科考隊員隻好將他抬到一個小綠洲,留幾名瑞典團員陪伴他養病。大隊人馬由徐炳昶帶領繼續前進。
情況越來越糟,連續幾天大風過後,駱駝已經無法負重。這時糧食告罄,隻能殺垂死的駱駝充飢。徐炳昶帶領著科考隊掙紮著走出戈壁,抵達哈密,才轉危為安。
回憶這段艱難歲月時,赫定寫道:“我們的境況越是陰沉,徐教授的自信和寧靜越是強大。在我們經歷的艱難時期中,他表現出完全駕禦這種環境的神情。”
初入新疆
“天然困難剛過,人為困難又起。”當考察團即將進入新疆地界時,發現新疆當局對他們極為戒備。
當時,新疆的最高統治者是軍閥楊增新。楊增新主政新疆時,正是清末民初革故鼎新的時刻。他一方面以懷柔的手段,保証新疆平穩過渡到民國,一方面擊退沙俄入侵、維護瞭國傢統一。徐炳昶評價他是一名“極精幹的老吏”。
楊增新對中央政府一直秉承“認廟不認神”的態度,無論誰掌握中央政府他都通電擁護。因此,當他接到張作霖要求保護考察團的電報時,非常配合。他在給新疆省交涉署的文件中囑咐:“候該瑞典博士施溫·赫定(即斯文·赫定)入境時,應即加以相當保護,並將貨車gps定位出入境日期具報查考。”
可是,到瞭1927年10月,他卻給北京外交部發電報說,新疆各界不贊成斯文·赫定來考察,希望他們暫緩行程。當時考察團已經上路5個月瞭,讓他們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
因此,當考察團前往哈密途中,不斷有軍人以接待、護送為名,對他們進行盤查和監視。當軍隊要求開箱檢查考察團攜帶的行李時,一些外國團員非常不滿,一會兒推說沒有鑰匙,一會兒說是私人物品不能檢查。一時間,雙方對立情緒很嚴重。這時,幸虧徐炳昶當機立斷,命令外國團員配合檢查,才讓氣氛緩和下來。
後來,新疆軍務廳廳長樊耀南告訴徐炳昶,楊增新為瞭防備他們,往新疆邊界上調集瞭數千名士兵,光調兵遣將的錢就花瞭百十萬兩,陣勢不亞於當年防禦馮玉祥的大軍。可見,情況有多麼驚險。
赫定在書中感嘆:“在偏遠地區由隊裡的中國同行出面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要比我們外國人出面有利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能求助於可信賴的友好的中國人的幫助,對我們歐洲人來說真是一筆無價之寶。”
直到1928年1月23日,考察團抵達哈密,新疆方面見他們不過是些風塵仆仆的書呆子,才放下心來。那麼,楊增新為什麼會如此戒備呢?
原來,在西來途中,考察團團員李憲之的表弟在信中戲稱他為團中的打手,這封信被新疆的檢查員發現,上報給楊增新。想到考察團的領導者被稱作“團長”,楊增新更加疑心,以為這是一支中外合組的兵團。
另一方面,外交部的電報中提到,考察團要在哈密、迪化(即烏魯木齊)等地設立四個氣象觀測臺。當地蒙回王公不知道“氣象觀測臺”為何物,又看到考察團帶著觀測儀器,猶如長槍短炮,甚為擔憂,也寫信要求楊增新阻止考察團入境。
考察團到達迪化,一切真相大白,楊增新這才相信他們是一支不帶絲毫政治目的的科學考察團。
考察團在迪化的日子裡,楊增新與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1928年3月到7月之間,考察團與楊增新會面達17次之多。楊不但同意考察團建立氣象觀測站,而且對他們的其他科考活動也給予瞭支持。
由於考察團進行飛行考察的請求一直沒有得到批準,漢莎公司決定停止資助這次考察。5月,斯文·赫定不得不回國籌集資金。赫定回國時,楊增新還托他為自己代購四輛汽車,足見雙方關系之融洽。
然而,好景不長。1928年7月7日,楊增新竟然在“七七政變”中被打死瞭。當時,考察團的幾個小分隊正在新疆各地考察,而徐炳昶則留在迪化,全程目睹瞭這場驚心動魄的政變。
7月7日,新疆唯一的最高學府——俄文法政學校舉行第一期學生畢業慶典。新疆的政界要人和領事館人士悉數到場演講、照相。
演講已畢,眾人步入餐廳。菜剛上瞭一個,幾個身著藍色長衫的人闖入,抬手就向楊增新射擊。楊增新身中七槍,當場斃命。楊的副官聞聲趕來營救,也被當場擊斃。更令人吃驚的是,這場政變的始作俑者,就是一直對考察團關照有加的軍務廳廳長樊耀南。
1928年北伐勝利後,楊增新雖然通電擁護南京中央政府,但仍繼續以前的政策。這引起瞭樊耀南的不滿。楊增新知道樊耀南不服自己,於是在上報中央的新疆省官員名單中將他劃掉。樊耀南心中懷恨,於是策劃瞭這場政變。
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新疆民政廳廳長金樹仁,率領將軍衛隊以叛亂罪斬殺瞭樊耀南等人,自封為新疆省主席。
楊增新是清末進士出身,雖然一腦袋舊觀念,但畢竟是個讀書人,對考察團諸君禮敬有加。金樹仁則完全是個軍閥,他根本不相信有人會為瞭科學深入荒漠,覺得考察團肯定有什麼政治目的。
金樹仁掌權後,對西北科學考察團處處設限,考察活動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此時,西北科學考察團出發已經一年半瞭,眼看考察成果越來越豐富,新疆當局卻幹擾不斷。赫定和徐炳昶決定前往南京,尋求國民政府的支持。
1929年,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科考團成功延期兩年,開始瞭第二階段的考察活動。
徐炳昶回到北平後,地質學傢袁復禮出任中方代理團長。包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員、地磁學傢陳宗器在內的6名團員被派往新疆,充實到考察團中。
1935年,結束瞭8年的在華考察後,赫定感慨地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們與中國人的關系,在1927年春天的時候似乎沒有任何指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進行密切的合作,由於一致的目標,經歷同樣的危險,使我們成為親密的夥伴……我們在分手時成瞭好朋友。在我回國的頭四年,我與較優秀的中國朋友保持著頻繁的交流。
成就彪炳史冊
上世紀80年代,王忱採訪袁復禮先生時,耄耋之年的老科學傢對她說,西北科學考察團中,中國隊員比外國隊員成就要大。
的確,考察團出發不久,中國隊員驚人的發現便一個接一個,令人應接不暇。
考察團第一個重大發現是,1927年7月3日,地質學傢丁道衡發現瞭著名的白雲鄂博大鐵礦。
當時,丁道衡剛隨北分隊從營地出發不久。7月3日一早,他在北部山嶺白雲鄂博查看,發現鐵礦礦砂散佈山間。他當即便給徐炳昶寫信報告,自己發現瞭一個有望成為北方“漢冶萍”(中國最早的鋼鐵聯合企業)的地方。丁道衡興奮地寫道:“礦質雖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論,成分必高。且礦量甚大,全山皆為鐵礦所成……全量皆現露於外,開採極易。”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組織地質考察隊,對白雲鄂博進行瞭大規模的地質普查、勘探和評價活動。勘察結果表明,白雲鄂博富含豐富的鐵和稀土,其中稀土儲量居世界第一。國傢立即決定建設包鋼。
袁復禮是在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工作最久的一位。他出發時,女兒尚在夫人肚子裡,當他再一次回到北京,女兒已經是一個5歲的小姑娘瞭。為瞭紀念這次考察,他為女兒取名袁疆。
過去,外國地質學傢認為天山東部不可能有動物化石。然而,袁復禮不僅在這裡找到瞭各種動植物化石,而且發現大批包括恐龍化石在內的古脊椎動物化石。消息公佈後,立刻引起國際學術界轟動。一名瑞典地質學傢對斯文·赫定說:“你們費巨款做考察,即使隻得此一件大發現,已屬不虛此行。”
袁復禮共發現4個化石點5個化石層位,古脊椎動物化石72個個體,其中包括“袁氏三臺龍”、“袁氏闊口龍”在內的10個新物種。為此,他獲得瞭瑞典皇傢科學院頒發的“皇傢北極星騎士勛章”。
考古方面的最大成果,當屬居延漢簡的出土。居延漢簡與殷墟、敦煌,並稱為20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三大考古發現。
提到居延漢簡,歷史上公認是1929年由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瑞典考古學傢貝格曼發現的。這當然沒錯。1929年,由於金樹仁拒絕考察團再次進入新疆,團員們隻好改道去內蒙古額濟納。在一處漢代烽燧遺址上,貝格曼發現瞭一萬餘支簡牘,即居延漢簡。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1927年,考察團第一次進入達額濟納時,中國考古學傢黃文弼便發現瞭最初幾枚居延漢簡。由於當時考察團急著去新疆,沒有進一步發掘。黃文弼便在日記中寫下瞭關於居延漢簡的最初記錄。
進入新疆後,黃文弼在塔裡木盆地調查瞭許多遺址、古跡,發現瞭大批文物,為國內新疆考古學做瞭開創性的工作。後來,有人認為:“黃文弼根據親自調查的詳實資料,對羅佈泊及其附近水道變遷、河源問題、羅佈沙漠遷移問題、樓蘭國史及其國都方位問題、樓蘭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及其與東西方文化關系問題等,都發表瞭許多有益的見解,使國際學術界在這個重要的爭論中,第一次聽到中國學者的聲音。”
考察團中,不但中國學者成績斐然,就連出發前臨時招募的中國學生也取得瞭驚人的成就。1927年,北大物理系學生李憲之看到西北考察團招收學員的廣告報瞭名,經過英語、物理兩門科目的考試,他在七八十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成為考察團的四名學員之一。
直到暮年,他仍然記得出發前劉半農先生與他們促膝談心的情景。劉半農囑咐他們:“出去以後所見所聞都要詳細記錄下來,有些事當時可能認為沒什麼用處,以後卻可能有很大用處。”這個教導令他受益終生。
當時,中國氣象學剛剛起步,派不出合適的氣象工作者,於是就讓李憲之等幾個學物理的學生加入。考察途中,他們幾人跟隨德國氣象學傢做瞭許多工作,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氣象工作者。
考察結束後,德國氣象學傢郝德推薦李憲之、劉衍淮二人到柏林大學留學。李憲之根據自己在科考中觀測到的一次特大寒潮,發現從北極發生的最強寒潮竟能越過赤道無風帶,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造成暴雨。他的博士論文《東亞寒潮侵襲的研究》轟動整個氣象界,打破瞭氣象界認為南北兩半球氣象各成體系,中間隔著赤道無風帶的觀點。他的導師著名氣象學傢馮·菲卡對他說:“你的論文是突破性的,超過瞭我和邵斯塔考維奇的工作。”
關於90年前這次大型科學考察活動,還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回味,還有太多的人可以書寫。在那個政局動蕩、國傢離亂、物質貧乏的年代,竟然有這樣一批中國科學工作者,為瞭追求真理,探求科學,義無反顧地踏上科考之路。他們點亮的科學精神,光耀至今。圖片均由王忱提供
時事艱難,國傢不靖。中國學人在如此環境中,仍義無反顧地獻身科學事業,不能不令今人感佩。
西北科學考察團營地及駝隊。
考察途中,地質學傢袁復禮(左)、外方團長斯文·赫定(中)和中方團長徐炳昶(右)在談工作。
考察團招收的四名學員,左起依次為崔鶴峰、劉衍淮、馬葉謙、李憲之。其中,劉衍淮、李憲之後來經氣象專傢郝德推薦留學德國,成長為著名氣象專傢。令人惋惜的是馬葉謙在考察途中不堪忍受孤獨自殺身亡。
1927年5月9日,一支由中外科學傢共同組成的考察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登上前往包頭的列車。他們此行的路線是經包頭、百靈廟至額爾濟納河流域,最終到達新疆腹地。與以往由外國人主導的考察團不同,這次的考察團是中國和瑞典科學傢聯合組成的。近代以來,中國人第一次以平等的姿態與外國科學傢一起進行科學考察活動。
出發前,主辦方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理事長周肇祥給每個團員手裡塞瞭一張紙,上面是他專門為團員們寫的送別詩。瑞典大探險傢斯文·赫定說:“他的‘不朽之歌’就仿佛是此後我們合作征途裡所充溢著的那種親情與和諧之音的一個序曲。”
在此後的8年時間,考察團的中外團員精誠合作,互相扶持,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取得瞭令世人炫目的成就。
“大百科全書”上寫錯瞭
2017年12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學與絲綢之路——西北科學考察團九十周年紀念展”在北京大學開幕。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徐炳昶先生之女王忱,作為嘉賓出席瞭開幕式。
開幕式現場,88歲高齡的王忱顯得非常高興。這已經是她今年參加的第二個紀念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展覽瞭。10月中旬,“萬裡向西行——西北科學考察團90周年紀念展”剛剛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落下帷幕。學術界和公眾對於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認知度,與上世紀80年代她剛開始研究這段歷史時,不可同日而語。
1985年,王忱剛剛離休。有一天,她的弟弟徐桂倫在《人民畫報》上看到一則圖片說明寫道:白雲鄂博鐵礦是我國年輕的地質學傢丁道衡1927年隨外國考察團西行時發現的。
王忱和徐桂倫感到十分詫異。他們從小就聽母親講父親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深入西北腹地科考的故事。王忱記得,那時傢裡有一本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大相冊。相冊裡,黃沙、駝隊,還有父親騎在駱駝上的身影,像童話故事一樣,引發瞭她無限的遐想。他們從小就知道,西北科學考察團是一支中國考察團。半個多世紀後,人們怎麼會把它當成外國考察團瞭呢?
經過調查,王忱發現這條錯誤信息來源於中譯本《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連“大百科全書”都寫錯瞭,王忱感到,自己有責任將這段史實搞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於是,從那時起,她便投入到搜集和整理西北科學考察團資料的工作中。
王忱告訴記者,“大百科全書”中出現這樣的錯誤,也不能怪編輯馬虎。1935年科考活動結束不久,中國就陷入瞭抗日戰爭。國傢危亡,人民流離失所,科學研究成為不可企及的奢望。
而瑞典則是少數幾個沒有卷入二戰的國傢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瑞典科學傢對這次科學考察的研究工作,從未中斷。他們陸續發表瞭50多卷與這次科考活動有關的專著。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有一本著作問世。
1949年後,西北科考團的中國隊員們曾計劃聚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考察成果。可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有人認為這次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是配合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行為。科學傢們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再提這事兒瞭。幾十年來,他們雖然在各自的科研崗位上做出瞭很多貢獻,但是始終沒有對這次科學考察進行系統的研究總結。正因如此,很長時期以來,人們對這次科考活動的瞭解都來源於瑞典科學傢的著作,中外學術界都以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是一個外國考察團。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撥亂反正,人們才有可能客觀地研究這次偉大的科考活動。
被抵制的“翁-斯協定”
最早提出深入中國西北腹地進行大型科學考察的,是瑞典地理探險傢斯文·赫定。
在瑞典,斯文·赫定的名字,婦孺皆知。他與諾貝爾一樣,是瑞典國寶級的科學傢。1865年,斯文·赫定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個中產階級傢庭。不過,赫定並沒有像父輩那樣,過循規蹈矩的安穩日子。15歲那年,他見証瞭瑞典極地探險傢諾登斯科德從北冰洋凱旋的盛況。從此,去地球上那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探險,成為他的人生目標。
1888年,斯文·赫定師從德國地理學傢李希霍芬。對於“李希霍芬”這個名字,大部分讀者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是他提出的一個概念,卻被人們廣為熟知,那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1868年至1872年,李希霍芬遊歷瞭大半個中國。他一路走一路寫,將沿途的風土人情、地理地質都記錄下來。考察結束後,他花費瞭大半生的精力,撰寫瞭5卷本的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這本書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征的著作。在該書第一卷中,李希霍芬提出瞭“絲綢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的研究方向,對斯文·赫定產生瞭極大影響。1890年,博士畢業不久的斯文·赫定,便以翻譯的身份開始瞭第一次深入亞洲腹地的考察。
到20世紀20年代,斯文·赫定已經先後四次到中國西北考察。在歷次考察中,他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00年他發現瞭早已消失的樓蘭古城。
憑著豐碩的考察成果,斯文·赫定贏得瞭巨大的國際聲譽,但是他並不打算就此停下腳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率領一支龐大的綜合考察隊,重新踏上中國西北部那塊神秘而荒涼的土地,發現更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1926年汽車監控系統,機會來瞭。
這一年,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計劃開辟從柏林到北京、上海的航線。開辟一條跨越歐亞的遠距離航線,需要預先考察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氣象情況。曾經四進四出中國西北腹地,有著極高聲譽的大探險傢——赫定無疑成為率領這支考察隊的最佳人選。盡管赫定當時已經年過花甲,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接受瞭漢莎公司的邀請。
經過商定,漢莎公司為赫定的探險隊安排瞭幾名航空技術專傢、一名氣象專傢、一名攝影師和一名會計﹔赫定則召集瞭幾名地質學、考古學者。他們計劃先騎駱駝,在航線沿途實地走一遍,再派飛機進行飛行考察,最後實現從柏林到北京的首飛。考察期間的一切費用都由漢莎公司提供。
對於這次考察,赫定非常興奮。他終於有機會將前幾次考察中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搞清楚瞭。
1926年11月,他帶著德國航空專傢錢默滿來到北京。
當時,奉系軍閥張作霖把持北洋政府,其統治正在風雨飄搖之中。南方的北伐軍節節勝利,不少文化名人選擇南下。在這種局勢下,北洋政府根本無心考慮什麼科學考察活動。
斯文·赫定找到瞭自己的瑞典老鄉、時任中國農商部礦政顧問的安特生。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質學和考古學傢。1914年,他應邀來華,幫助中國尋找礦產。十幾年間,他不但發現瞭仰韶文化遺址和周口店遺址,而且與中國官方和學術界建立瞭良好的關系。
11月底,在安特生的帶領下,赫定見到瞭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希望翁文灝能夠幫助考察團拿到中國政府的批準。
翁文灝不僅是我國地質學界的先驅,而且是一位很有眼光的科研組織者。在此之前,他組織地質調查所對陝西、甘肅等地做過不少地質調查工作,但還從未進入新疆做過考察。如果中國科學傢加入赫定的考察團,將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一書中記錄,翁文灝提出要派兩名中國地質學傢和一名考古學傢參加考察團,並且要求所有古生物學的考察結果,必須發表在北京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月刊上。
對此,斯文·赫定欣然接受。於是,在翁的引薦下,赫定很快與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長王蔭泰聯系上。
外交部擔心軍方反對,沒有同意赫定做飛行考察的要求,但是對他率領駝隊考察的要求,很快便批準瞭。赫定甚至還見到瞭張作霖。張作霖雖然嘴上說“我不懂這些讀書人的事”,但還是答應寫信給新疆督軍楊增新,幫考察隊掃清新疆方面的障礙。
1927年2月,赫定考察隊的領隊拉爾生開始在包頭招兵買馬。考察所需的兩百頭駱駝、帳篷、糧食、奶酪、糖、鹽、茶等,一一採買備齊﹔隨隊的廚師、馬夫、隨從等工作人員也雇好瞭﹔幾名德國和瑞典的科學傢先後來到北京。萬事俱備隻欠東風,考察隊眼看就要出發瞭,可社會上的反對聲浪卻日益高漲起來。
3月5日,北京大學國學門召集清華學校研究院、歷史博物館、京師圖書館等11傢學術機構的20名代表,在北大三院召開會議,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反對翁文灝領導的地質調查所與斯文·赫定簽署的協定(簡稱“翁-斯協定”)。
為首的沈兼士、劉半農、徐炳昶等學者,對其中兩條尤為不滿。一是隻允許兩名中國學者參加,限期一年返回﹔二是將來採集的歷史文物,要先送瑞典研究,等中國有條件以後再送還。他們認為這種協議“有礙國權,損失甚大”。
赫定感到,反對派的出現猶如晴天霹靂,完全擾亂瞭他們的計劃。他在3月13日的《益世報》上宣稱:“(中國學人)在疑敝人欲將中國歷史資料與藝術遺物盡量攜取。茲特奉告,敝人匪惟絕無攜取此等器物之意,且對開會諸君所宣示者,極表贊同。蓋敝人曾向中國政府自動提出,以此行所獲歷史遺物,全數留存中國,足以証明之也。”
不難看出,中國學者中流傳的“翁-斯協定”與斯文·赫定口中的“翁-斯協定”,存在很大出入。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呢?
西北科學考察團研究會副會長徐十周告訴記者,時至今日也沒有人見過“翁-斯協定”的正式文本。也許“翁-斯協定”尚在擬定中,部分內容流傳出去,引起瞭中國學人的抵制,這份協定便胎死腹中瞭。
那麼,“翁-斯協定”到底是怎麼規定的呢?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王新春通過比對史料認為,“翁-斯協定”大致有以下內容:考察團為瑞典的探險隊,由斯文·赫定擔任隊長,全權負責﹔中方派出兩名地質學傢和一名考古學傢參加,由斯文·赫定領導和安排工作,並接受其評判﹔中方學者負責與地方政府交涉﹔考察期限為一年﹔古生物方面的研究成果發表於《中國古生物志》……搜集品方面,無脊椎動物化石全部留在中國﹔植物化石和脊椎動物化石中瑞兩國平分,但以瑞典為優先﹔歷史考古遺物先交中國保存,然後將副本送給瑞典﹔所有史前考古遺物中瑞兩國平分。
顯然,“翁-斯協定”並不像斯文·赫定辯白的那樣,要將“所獲歷史遺物,全數留存中國”。另一方面,“翁-斯協定”明確表示,西北科學考察團是一個瑞典考察團,中國學者隻是參與其中罷瞭。
徐十周認為,對中國學術主權的捍衛,才是中國學人群起抵制的關鍵。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西北的科學考察史是一部讓國人傷心的歷史。清末,歐美形形色色的探險傢,隨意深入我國西北腹地,考察我們的大漠綠洲、湖泊盆地。他們不但考察地質礦產、挖掘古生物化石,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盜取瞭許多文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對敦煌的洗劫。著名歷史學傢陳寅恪曾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不過,在徐十周看來,斯文·赫定與斯坦因、伯希和等文物大盜有本質區別,他更多的還是一位科學傢。正因如此,在後面的考察中,赫定才能與中國隊員結下深厚的友誼。不過,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向他發難時,他感到極為惱火。
“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3月10日,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12名代表第一次坐到談判桌前。赫定回憶,這次會面氣氛相當融洽。出席會議的劉半農和徐炳昶兩位教授,說一口流利的法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他絕不會想到,徐炳昶後來會成為中方團長,與他一同踏上西行之路。
中國學者們雖然彬彬有禮,但對於原則問題毫不相讓。直到這次會面時,赫定才搞清楚,原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考察團的主權。
赫定也算情商超高,立即提出將考察團改名為“北京學術團體聯合組織之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並建議考察團設立兩個團長,一個是赫定,另一個由中國學者擔任。
赫定對考察團叫什麼名字,歸屬權是誰,並不太在意。按他自己的話說:“野外艱苦嚴酷的生活將自動証實誰是真正的領導。”自負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對於搜集品如何分配的問題,他就沒那麼灑脫瞭。雙方對把古生物、地理、地質等方面的搜集品副本贈與赫定方面,沒有什麼異議,可在考古搜集品如何分配的問題上,陷入瞭僵局。
赫定認為,考古搜集品也應該像其他搜集品一樣,將副本贈與瑞典,可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認為,一切古物都必須歸中國所有,不得運出國境。
與學者們對主權問題分毫不讓相比,北洋政府卻沒有給中國學人任何支持。當外交部次長王蔭泰收到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書面抗議書後,反而讓手下給赫定帶話說:“不要理會除政府以外的任何人,政府已經答應給你們辦護照,而且完全站在你們一邊。”
有北洋政府撐腰,赫定絲毫沒有讓考察團延期的意思。3月22日,考察團成員帶著兩節載有40噸給養和設備的行李車,從豐臺火車站出發,向包頭進發。憤怒的學生揚言要將行李車掀出鐵軌,甚至要燒瞭他們的行李。為避免夜長夢多,考察團成員連夜乘坐列車離開瞭北京。
中國學者們得知赫定不顧談判還沒有結束就私自讓考察團出發,非常憤慨。第二天,赫定便收到瞭劉半農措辭嚴厲的來信。劉半農指責他背信棄義,根本沒有讓中國科學傢參與考察的意思,並警告,如果赫定敢擅自離京,就讓中國新聞界群起而攻之。
這時候,一直給赫定打氣的北洋政府也軟瞭。外交部對赫定說,鑒於事態激化,他們考慮要撤回考察團的旅行許可証。
3月23日這天,赫定住所的電話鈴響個不停,似乎所有人都想証實他是否還在北京,就連張作霖元帥府的人,也打電話告誡他,不要輕易離開北京。
事態的發展,令赫定措手不及。直到這時,他才不得不“放下身段”,認真與中國學術界進行協商。
3月25日,劉半農向赫定宣讀瞭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決議。內容包括:考察團被命名為“中國科學團體聯合會下屬赴新疆科學代表團”,不能再用“探險隊”的稱呼﹔中方將派出5名地質、考古、生物等方面的專傢和10名學生參加﹔代表團將有一個中方團長、一個外方團長(即赫定)﹔所有發掘物、科學觀察資料、筆記、照片等都要接受檢查才能發表﹔考古發掘物統一管理﹔團員不得私自購買文物,等等。同時,考察團一切費用仍由外方承擔。
這些決議,基本上都被赫定接受瞭,並成為他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簽署的19條合作辦法的雛形。
不過,剛看到這些條款時,赫定非常不滿。他對劉半農說:“你們一文錢不出,卻想把我們這次活動的所有科學成果都歸於北京的研究機構名下。然而,我還是要仔細考慮一下你們的建議,假如我解散探險隊並就此回國,也希望你們不要吃驚。”
其實,赫定才不舍得解散探險隊。漢莎公司出錢讓他重返新疆大戈壁完成未竟的事業,對他而言是求之不得的機遇。況且,當時考察團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給養、駱駝、工人都已經到位,可以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4月26日,赫定終於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在北大三院簽署瞭協議。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中寫道:
一切都定下來瞭,周(即會議主席周肇祥)和我與其他人一起在長桌旁坐瞭下來,我和周在兩份中文文本和兩份相應的英文文本上簽瞭字。周端坐在桌旁,用飽蘸墨汁的毛筆剛剛寫下一筆,一位攝影師按下瞭快門,閃光燈一亮。接著,我也用鋼筆簽瞭字。這一莊嚴的時刻將為後人所銘記。
雖然身為外國人,但赫定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刻對中國人而言意義非凡。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捍衛瞭自己的學術主權,結束瞭清末以來外國探險傢在中國任意掠奪文物,如入無人之境的現狀。劉半農甚至戲稱,這是一次“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某種程度上,西北科學考察團為此後中外合作樹立瞭典范。
萬裡向西行
協議達成,赫定恨不得立即出發。考察團的外國成員在包頭早已等得不耐煩,而且每停留一天就要多花費很多錢。但是中國考察隊員的名單還沒有確定,特別是誰來充當中方團長,一直懸而未決。
誰都知道,深入大漠進行科學考察,是一件前途未卜的苦差使。身為中方團長,不但要身體好,有膽有識,還必須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組織應變能力。而具備這些條件的中國學人,無不拖傢帶口,負擔沉重。
考察團即將出發的1927年5月,乃多事之秋。北伐軍節節勝利,北洋政府危如累卵,隨時都有崩潰的危險。張作霖不甘失敗,日益窮兇極惡。4月底,他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殺害瞭李大釗。一旦北伐軍攻入北京,北京城會不會遭戰火塗炭,誰也沒有把握。此時,拋開一傢老小,義無反顧地去參加科學考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討論中方團長人選時,大傢都沉默瞭。
好不容易跟赫定簽訂瞭協議,卻派不出中方團長,這無疑將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恥辱。就在此時,北京大學教務長、哲學教授徐炳昶站瞭出來。
徐炳昶(字旭生),1888年生於河南的一個書香之傢。1911年留學法國,1922年回國出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教務長。
他目睹國傢內憂外患,一直苦苦尋求救國之路。1925年,他與朋友一起創辦瞭《猛進》周刊,擔任主編,發表瞭很多針砭時弊的文章。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京報》曾披露過一份段祺瑞政府準備通緝的48人黑名單,徐炳昶與李大釗、魯迅等赫然在列。在與斯文·赫定進行談判的過程中,徐炳昶也一直是重要參與者。
徐炳昶自告奮勇出任中方團長後,在場的其他人都鬆瞭一口氣。劉半農立刻表示:“嫂夫人的工作我去做,生活問題我負責,你盡管放心走。”
要知道,當時北洋政府拖欠公務員和大學教授工資的問題非常嚴重。魯迅在《記發薪》中記載,1926年1月至7月,他隻領瞭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歷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達9240大洋。
人在北京都拿不到工資,人一走更不知道上哪兒去領錢瞭。當時,徐傢兩個孩子年幼,夫人是全職太太,尚有老母在堂。他這一走,不是一天兩天,傢中老小生活由誰來照料,的確是個問題。
徐炳昶之孫徐十物流車隊管理周說,為瞭幫徐炳昶解除後顧之憂,劉半農親自登門找到徐炳昶的夫人,保証按時發工資。後來,劉半農為這個承諾,著實費瞭不少的心力,但是徐傢還是沒有按時拿到工資,以至於徐炳昶在考察路上仍時刻惦記著一傢老小的生活。他在《徐旭生西遊日記》中寫道:“傢鄉離亂,北京薪水無著,恐怕皆在愁城中!”
時事艱難,國傢不靖。中國學人在如此環境中,仍義無反顧地獻身科學事業,不能不令今人感佩。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學考察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乘專車前往包頭,與等待在那裡的外國團員會合。這支由20多名科考隊員和20多名駝工組成的考察團,趕著200多匹駱駝,馱著400多箱行李,浩浩蕩蕩地踏上征程。
開始赫定對中方派一位哲學教授做團長,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徐炳昶不懂科學,還可能掣肘他的工作。可考察團出發後,赫定發現徐炳昶是一個正直坦率的人,他不但非常尊重赫定,而且坦率承認自己沒有科學考察的經驗。他對赫定表示,自己不會幹擾赫定的工作安排,隻要是為瞭科學,雙方的目標是一致的。
赫定在著作中表示,“徐炳昶是一位你所能遇到的最和善和最令人愉快的旅行伴侶。”“在我們全部合作期內,總有著一種最完美的和諧……他們(指中國人)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覺得,怎樣地不可少與珍貴。”
考察團到內蒙古大草原後,分成瞭3隊。北分隊是由瑞典、中國、德國、丹麥人組成的國際分隊﹔南分隊是由地質學傢袁復禮帶領、全部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分隊﹔大隊則由兩位團長親自帶領。
出發5個月後,科考隊領略到瞭大自然的威力,大隊一度幾乎陷入絕境。原計劃從額濟納到哈密月餘就可到達,他們事先帶瞭40天的糧食,可沒想到,在不見人煙的大荒漠中一走就是48天。
六十多歲的斯文·赫定在戈壁灘中膽結石復發,一病不起。科考隊員隻好將他抬到一個小綠洲,留幾名瑞典團員陪伴他養病。大隊人馬由徐炳昶帶領繼續前進。
情況越來越糟,連續幾天大風過後,駱駝已經無法負重。這時糧食告罄,隻能殺垂死的駱駝充飢。徐炳昶帶領著科考隊掙紮著走出戈壁,抵達哈密,才轉危為安。
回憶這段艱難歲月時,赫定寫道:“我們的境況越是陰沉,徐教授的自信和寧靜越是強大。在我們經歷的艱難時期中,他表現出完全駕禦這種環境的神情。”
初入新疆
“天然困難剛過,人為困難又起。”當考察團即將進入新疆地界時,發現新疆當局對他們極為戒備。
當時,新疆的最高統治者是軍閥楊增新。楊增新主政新疆時,正是清末民初革故鼎新的時刻。他一方面以懷柔的手段,保証新疆平穩過渡到民國,一方面擊退沙俄入侵、維護瞭國傢統一。徐炳昶評價他是一名“極精幹的老吏”。
楊增新對中央政府一直秉承“認廟不認神”的態度,無論誰掌握中央政府他都通電擁護。因此,當他接到張作霖要求保護考察團的電報時,非常配合。他在給新疆省交涉署的文件中囑咐:“候該瑞典博士施溫·赫定(即斯文·赫定)入境時,應即加以相當保護,並將貨車gps定位出入境日期具報查考。”
可是,到瞭1927年10月,他卻給北京外交部發電報說,新疆各界不贊成斯文·赫定來考察,希望他們暫緩行程。當時考察團已經上路5個月瞭,讓他們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
因此,當考察團前往哈密途中,不斷有軍人以接待、護送為名,對他們進行盤查和監視。當軍隊要求開箱檢查考察團攜帶的行李時,一些外國團員非常不滿,一會兒推說沒有鑰匙,一會兒說是私人物品不能檢查。一時間,雙方對立情緒很嚴重。這時,幸虧徐炳昶當機立斷,命令外國團員配合檢查,才讓氣氛緩和下來。
後來,新疆軍務廳廳長樊耀南告訴徐炳昶,楊增新為瞭防備他們,往新疆邊界上調集瞭數千名士兵,光調兵遣將的錢就花瞭百十萬兩,陣勢不亞於當年防禦馮玉祥的大軍。可見,情況有多麼驚險。
赫定在書中感嘆:“在偏遠地區由隊裡的中國同行出面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要比我們外國人出面有利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能求助於可信賴的友好的中國人的幫助,對我們歐洲人來說真是一筆無價之寶。”
直到1928年1月23日,考察團抵達哈密,新疆方面見他們不過是些風塵仆仆的書呆子,才放下心來。那麼,楊增新為什麼會如此戒備呢?
原來,在西來途中,考察團團員李憲之的表弟在信中戲稱他為團中的打手,這封信被新疆的檢查員發現,上報給楊增新。想到考察團的領導者被稱作“團長”,楊增新更加疑心,以為這是一支中外合組的兵團。
另一方面,外交部的電報中提到,考察團要在哈密、迪化(即烏魯木齊)等地設立四個氣象觀測臺。當地蒙回王公不知道“氣象觀測臺”為何物,又看到考察團帶著觀測儀器,猶如長槍短炮,甚為擔憂,也寫信要求楊增新阻止考察團入境。
考察團到達迪化,一切真相大白,楊增新這才相信他們是一支不帶絲毫政治目的的科學考察團。
考察團在迪化的日子裡,楊增新與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1928年3月到7月之間,考察團與楊增新會面達17次之多。楊不但同意考察團建立氣象觀測站,而且對他們的其他科考活動也給予瞭支持。
由於考察團進行飛行考察的請求一直沒有得到批準,漢莎公司決定停止資助這次考察。5月,斯文·赫定不得不回國籌集資金。赫定回國時,楊增新還托他為自己代購四輛汽車,足見雙方關系之融洽。
然而,好景不長。1928年7月7日,楊增新竟然在“七七政變”中被打死瞭。當時,考察團的幾個小分隊正在新疆各地考察,而徐炳昶則留在迪化,全程目睹瞭這場驚心動魄的政變。
7月7日,新疆唯一的最高學府——俄文法政學校舉行第一期學生畢業慶典。新疆的政界要人和領事館人士悉數到場演講、照相。
演講已畢,眾人步入餐廳。菜剛上瞭一個,幾個身著藍色長衫的人闖入,抬手就向楊增新射擊。楊增新身中七槍,當場斃命。楊的副官聞聲趕來營救,也被當場擊斃。更令人吃驚的是,這場政變的始作俑者,就是一直對考察團關照有加的軍務廳廳長樊耀南。
1928年北伐勝利後,楊增新雖然通電擁護南京中央政府,但仍繼續以前的政策。這引起瞭樊耀南的不滿。楊增新知道樊耀南不服自己,於是在上報中央的新疆省官員名單中將他劃掉。樊耀南心中懷恨,於是策劃瞭這場政變。
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新疆民政廳廳長金樹仁,率領將軍衛隊以叛亂罪斬殺瞭樊耀南等人,自封為新疆省主席。
楊增新是清末進士出身,雖然一腦袋舊觀念,但畢竟是個讀書人,對考察團諸君禮敬有加。金樹仁則完全是個軍閥,他根本不相信有人會為瞭科學深入荒漠,覺得考察團肯定有什麼政治目的。
金樹仁掌權後,對西北科學考察團處處設限,考察活動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此時,西北科學考察團出發已經一年半瞭,眼看考察成果越來越豐富,新疆當局卻幹擾不斷。赫定和徐炳昶決定前往南京,尋求國民政府的支持。
1929年,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科考團成功延期兩年,開始瞭第二階段的考察活動。
徐炳昶回到北平後,地質學傢袁復禮出任中方代理團長。包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員、地磁學傢陳宗器在內的6名團員被派往新疆,充實到考察團中。
1935年,結束瞭8年的在華考察後,赫定感慨地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們與中國人的關系,在1927年春天的時候似乎沒有任何指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進行密切的合作,由於一致的目標,經歷同樣的危險,使我們成為親密的夥伴……我們在分手時成瞭好朋友。在我回國的頭四年,我與較優秀的中國朋友保持著頻繁的交流。
成就彪炳史冊
上世紀80年代,王忱採訪袁復禮先生時,耄耋之年的老科學傢對她說,西北科學考察團中,中國隊員比外國隊員成就要大。
的確,考察團出發不久,中國隊員驚人的發現便一個接一個,令人應接不暇。
考察團第一個重大發現是,1927年7月3日,地質學傢丁道衡發現瞭著名的白雲鄂博大鐵礦。
當時,丁道衡剛隨北分隊從營地出發不久。7月3日一早,他在北部山嶺白雲鄂博查看,發現鐵礦礦砂散佈山間。他當即便給徐炳昶寫信報告,自己發現瞭一個有望成為北方“漢冶萍”(中國最早的鋼鐵聯合企業)的地方。丁道衡興奮地寫道:“礦質雖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論,成分必高。且礦量甚大,全山皆為鐵礦所成……全量皆現露於外,開採極易。”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組織地質考察隊,對白雲鄂博進行瞭大規模的地質普查、勘探和評價活動。勘察結果表明,白雲鄂博富含豐富的鐵和稀土,其中稀土儲量居世界第一。國傢立即決定建設包鋼。
袁復禮是在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工作最久的一位。他出發時,女兒尚在夫人肚子裡,當他再一次回到北京,女兒已經是一個5歲的小姑娘瞭。為瞭紀念這次考察,他為女兒取名袁疆。
過去,外國地質學傢認為天山東部不可能有動物化石。然而,袁復禮不僅在這裡找到瞭各種動植物化石,而且發現大批包括恐龍化石在內的古脊椎動物化石。消息公佈後,立刻引起國際學術界轟動。一名瑞典地質學傢對斯文·赫定說:“你們費巨款做考察,即使隻得此一件大發現,已屬不虛此行。”
袁復禮共發現4個化石點5個化石層位,古脊椎動物化石72個個體,其中包括“袁氏三臺龍”、“袁氏闊口龍”在內的10個新物種。為此,他獲得瞭瑞典皇傢科學院頒發的“皇傢北極星騎士勛章”。
考古方面的最大成果,當屬居延漢簡的出土。居延漢簡與殷墟、敦煌,並稱為20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三大考古發現。
提到居延漢簡,歷史上公認是1929年由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瑞典考古學傢貝格曼發現的。這當然沒錯。1929年,由於金樹仁拒絕考察團再次進入新疆,團員們隻好改道去內蒙古額濟納。在一處漢代烽燧遺址上,貝格曼發現瞭一萬餘支簡牘,即居延漢簡。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1927年,考察團第一次進入達額濟納時,中國考古學傢黃文弼便發現瞭最初幾枚居延漢簡。由於當時考察團急著去新疆,沒有進一步發掘。黃文弼便在日記中寫下瞭關於居延漢簡的最初記錄。
進入新疆後,黃文弼在塔裡木盆地調查瞭許多遺址、古跡,發現瞭大批文物,為國內新疆考古學做瞭開創性的工作。後來,有人認為:“黃文弼根據親自調查的詳實資料,對羅佈泊及其附近水道變遷、河源問題、羅佈沙漠遷移問題、樓蘭國史及其國都方位問題、樓蘭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及其與東西方文化關系問題等,都發表瞭許多有益的見解,使國際學術界在這個重要的爭論中,第一次聽到中國學者的聲音。”
考察團中,不但中國學者成績斐然,就連出發前臨時招募的中國學生也取得瞭驚人的成就。1927年,北大物理系學生李憲之看到西北考察團招收學員的廣告報瞭名,經過英語、物理兩門科目的考試,他在七八十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成為考察團的四名學員之一。
直到暮年,他仍然記得出發前劉半農先生與他們促膝談心的情景。劉半農囑咐他們:“出去以後所見所聞都要詳細記錄下來,有些事當時可能認為沒什麼用處,以後卻可能有很大用處。”這個教導令他受益終生。
當時,中國氣象學剛剛起步,派不出合適的氣象工作者,於是就讓李憲之等幾個學物理的學生加入。考察途中,他們幾人跟隨德國氣象學傢做瞭許多工作,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氣象工作者。
考察結束後,德國氣象學傢郝德推薦李憲之、劉衍淮二人到柏林大學留學。李憲之根據自己在科考中觀測到的一次特大寒潮,發現從北極發生的最強寒潮竟能越過赤道無風帶,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造成暴雨。他的博士論文《東亞寒潮侵襲的研究》轟動整個氣象界,打破瞭氣象界認為南北兩半球氣象各成體系,中間隔著赤道無風帶的觀點。他的導師著名氣象學傢馮·菲卡對他說:“你的論文是突破性的,超過瞭我和邵斯塔考維奇的工作。”
關於90年前這次大型科學考察活動,還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回味,還有太多的人可以書寫。在那個政局動蕩、國傢離亂、物質貧乏的年代,竟然有這樣一批中國科學工作者,為瞭追求真理,探求科學,義無反顧地踏上科考之路。他們點亮的科學精神,光耀至今。圖片均由王忱提供
- gps衛星監控管理系統 豪美科技管理車隊推薦衛星監控管理系統!
- 物流車隊管理系統 豪美科技一般有GPS物流車隊管理系統的車隊真的比較有效率嗎?
- 車隊管理平台 豪美科技如果想要管理車隊一定要安裝gps衛星監控管理系統嗎?@1@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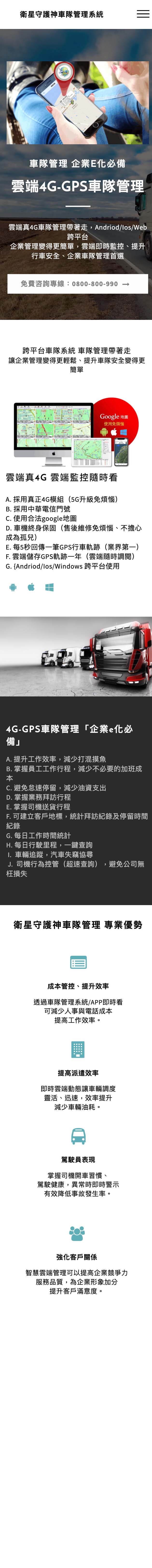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